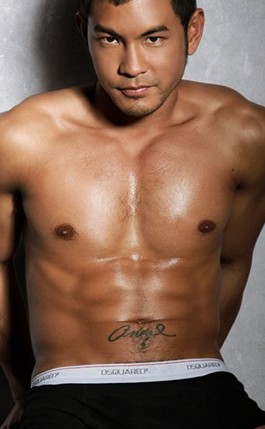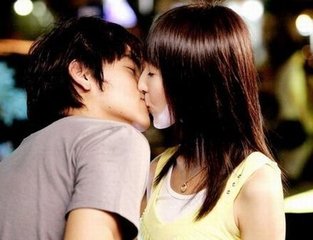奮斗是逼出來的
學中文讀到大學畢業,寫出幾篇好文章,那不叫奮斗,那叫本分。
奮斗或許是基于某種理想,而理想若能順利實現,也無須去奮斗。因此我們要說,奮斗是逼出來的。
不是硬要謅句什么格言以欺世,實在是得自大半生艱辛。
我是上過大學的,學的是歷史,按文史不分的通識,寫文章該是本分。然而,那是怎樣的上學。學制五年,倒有上年半是在文革中度過的,沒上過一堂課,沒發過一頁講議。到了1970年夏天,說畢業就畢業了,分配到呂梁山里的一個村子教書。六年級,二十幾個學生,在一個破舊的窯洞里上課。后來去了別的村里,教的是初中、高中。
就這么教下去嗎?本地教員,可以服務桑梓而自慰,而我,家在數百里之外,妻子又不可能調來,真要到了老年……別說真的了,想想都害怕。
不行,得離開這個地方。
背著出身不好的惡名,沒有關系可憑憑靠,就是有也沒有錢財可疏通,惟一的途徑,只能是靠自己努力。偶爾看到一本《革命文藝》,是省文化館編的,見上面有篇東西像是小說,眼睛一亮,何不寫上一篇也寄去試試。若真的能以此顯出本事,領導看重說不定會調回縣城,說不定會放我回老家去教書。一支筆幾張紙就行了,縱然一無所成,也沒有損失什么。
寫吧,常是晚上下了自習后開始,在窯洞里,在煤油燈下。
第一篇發表后,信心陡增,便接連寫下去。粉碎四人幫后,刊物多了,寫作的勁頭更足了。白天寫怕人說三道四,多是等學生下了晚自習再寫。有時寫到凌晨三四點,明明瞌睡得快要睜不開眼,也不敢上床,一睡著準會耽擱出早操。只好點上一支煙,端坐在桌子前,靜待起床鐘響,出去帶領學生出早操。出完操,還得檢查早自習,若上午沒課,還可以睡一會兒,若上午有課,那就只能等到午后了。
就這樣,有兩三年的時間,寫小說,寫散文,凡是報刊上登載的文學作品,除了詩我都寫過。也有退稿,我的老主意是,退只管你退,寫只管我寫。我不是聰明人,可無論怎么說也是個勤勉的人。勤不光能補拙,勤還可以悟道。比如抄稿太誤事,便想到,何不訓練自己一次成文。不是先想好再寫,那是不可能的,而是錯了就錯了,接下來補足。魯迅先生的《祝福》中有這樣的句子:籃子里有個碗,破的我給學生講語法時,說這是一種倒置,心里卻在思謀,極有可能是先生寫下碗字,覺得該對碗有個說明,便順手寫了破的補足。只要不是大錯,用這種辦法,常能收到意外的表達效果。
經過長時間的辛苦磨練,總算熬出來了。
現在我還在寫作,只是這樣的寫作,已不能稱之為奮斗了,該說是職責或是本分。只是偶然間,還會想起自己當年的奮斗,還會生出那種奮斗的激情。
【】【 】【】【】 上一篇文章:下一篇文章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