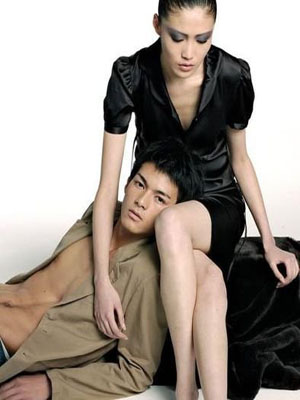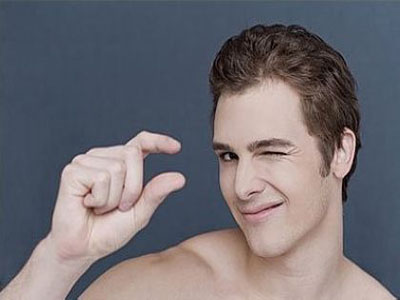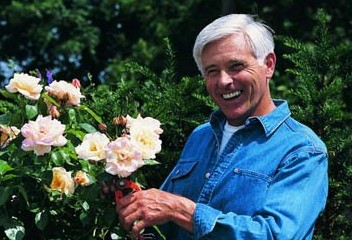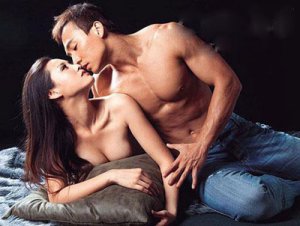面子和幸福,你選擇哪一個
對中國人來說,“面子”是個特別重要的東西。比方說“餓死事小,失節事大”。在很多情況下,這個“節”指的不是“氣節”而是“面子”。飯桌上搶著結帳、借巨款娶媳婦、不好意思向朋友討債、把僅剩的工資拿去“湊份子”等等。“不要面子”或“丟了面子”是很嚴重的,它往往意味著被議論、指責甚至受歧視。因為這個“面子”,中國人活得比別人都累。
我自己也很要面子,為此吃過不少苦頭,可這毛病還是很難改,因為我就是受這樣的教育長大的,因為我一直生活在這樣一個傳統、一個環境里——我們文化傳統的有些地方好像不大對勁兒。傳統的儒家倫理是這樣教育我們的:我們每個人都不是獨立的人而是集體中的一分子;一個獨立的“個人”沒有價值,“個人”的價值是“集體”給你的。因此你自己怎樣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這個“集體”如何看待你。所以你永遠得靠別人對你做出評價——你到底是什么、到底怎么樣要由別人說了算。這種觀念聽上去顯然有問題,可我們很少懷疑過。所以生活在別人挑剔的目光下,我們自然都“很要面子”。身為中國人,誰又沒干過幾件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的事兒呢?
為了“面子”受些小罪、損點小錢倒還問題不大,但有時候我們實在承受不了“要面子”的代價。對于許多ED患者來說就是這樣。
調查表明,有些患者是因為“怕丟面子”而不愿或不敢就診的。其實,治療他們的ED并不難,難的是清除這個心理方面的障礙。這已經成了ED醫療方面的一個大問題。但與這些患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,在相當一部分患者身上卻不存在這樣的問題。發現患病后,他們想都沒想就走進了醫院。這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很自然的、根本用不著去考慮的事情。這樣的案例引起了研究人員和醫生們的興趣——搞清楚他們的心態也許對其他患者會有很大的幫助。
有一位患者接受采訪,談他對ED這一疾病的看法和自己就診、治療的過程、感想,而且是和妻子一同接受電視記者的采訪。采訪開始前,偌大的房間非常安靜,可以聽得見攝像機倒帶的聲音,氣氛緊張而壓抑。刺眼的燈光直射著患者,他的表情卻出人意料地輕松。采訪開始后,由于涉及很“私密”的問題,倒是記者顯得比患者還要緊張。整個采訪過程中,患者完全沒有負擔,非常從容、坦率地回答了記者的每一個提問。最后,記者問:“您第一次去醫院看病的時候有沒有覺得不好意思或者難于啟齒?”他說:“沒有!”記者又問:“一點兒都沒有嗎?”他回答:“一點兒都沒有!”記者顯然有些不理解:“那為什么呢?”他想都不想就回答說:“得病了嘛,就該去治,對醫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?我又沒做什么錯事,不過是得了病,有什么不能說的?再說,你要是不好意思,不去治,病不是越來越重嗎?到頭來倒霉的不還是自己?你說是不是?……”
他的道理簡單得讓人有些吃驚。可仔細想想,它的確直指問題的核心。我們忙碌地奔波在世界上,忍受著糟糕的環境、繁重的工作、單調的生活節奏、復雜的人際關系……我們為什么?不就是為了生活得好一些——生活得幸福一些?我們不得不接受的東西已經這么多,我們已經忍受了這么多,我們已經付出了這么多,還有誰能剝奪我們這一點點追求健康、幸福的權利呢?那些在遠處用挑剔的目光審視著我們生活的人,他們能嗎?不,他們不能!面子是做給別人看的——所以它也被叫作“虛榮”,“虛”的意思就是虛假、虛幻和不真實的;但生活是我們自己的,它真實的、可靠、無法回避。無論幸福或者不幸,只有我們自己承受它、為它負責。 為“面子”所困的時候,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遠離、忘掉那些審視我們的人,把目光真正投向自己、投向自己的生活。有一位患者很無奈也很憤怒地說:“我自己也覺得該去治療,也覺得這個病沒什么特別的,可別人不這么看呀!”別去想“別人”了。這種時候,就只當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吧——的確是只有你一個人,只有你應該并且能夠為自己的幸福負責。
這么做并不難,已經有很多人做了他們應該做的,并為此感到慶幸。那位和妻子一起接受采訪的患者病情已經大大好轉,現在仍定期去醫院接受檢查和治療。他接受采訪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感想告訴大家。他說:“只要我當初稍微猶豫那麼一點,可能就把自己耽誤了。”
是的,不能選擇錯誤,也不能猶豫。有一位西方著名的哲學家曾說過一句話,給我的印象非常深:“在面臨決斷的時候你往往有三種選擇,第一種是選擇此,第二種是選擇彼,第三種是什么也不選擇。其實“什麼都不選擇”也是一種選擇,而且恰恰是最糟糕的。”
身為中國人,誰又沒做過幾件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的事呢?什么都不選擇……其實這正是最糟糕的一種選擇。比如我在沙漠里迷了路,必須選擇向左還是向右走,如果我就那么站著,恐懼、猶豫不決直至放聲大哭,那也只有等死了……
傳統的儒家觀點教育我們說,人永遠不是個體,而只是一群人中間的一個,你就是這個永遠沒法獨立的人,所以,你永遠得靠別人來給自己作出評價,也就是說,你到底是什么要由別人說了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