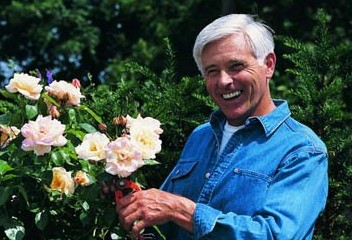門戶不當的夫妻終究難逃離婚
【傾訴人】姚昆男38歲技術員
還沒走到餐廳,就已經透過玻璃窗看到了姚昆,西裝筆挺的模樣,顯然經過了一番打扮。看我推門進來,他微微起身,匆匆地整理著手中那份他在家已列好的談話提綱。“我老婆瞧不起我,很早以前我就知道,可一直忍著沒說,就是為了保全這個家,可事到如今,婚姻終究是難逃一劫啊!”他的聲音低低的,那里面有懊惱、有遺憾,也有不服……
學歷高是我選擇她做妻子的原因
1984年,我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考進了鄭州一所中專。4年求學,新奇又富于挑戰,但我始終不敢大意,年年考試都是前幾名。畢業后工作,在工地里搞基礎施工,雖然辛苦但也充實,每當看到一棟棟大樓拔地而起時,心里還有那么一點點成就感。每月我會按時往家里寄錢,向操勞一輩子的父母表示一下我的孝心。可父母總是說家里千好萬好,讓我把錢省下來早點解決個人問題。我明白父母的心思,也信誓旦旦地跟他們保證一定會娶個好媳婦。可是在鄭州這幾年,我總是東奔西跑的,談何戀愛呢。
那天,一條消息打破了我原本平靜的生活。一個初中時成績不如我的同學,大學畢業后竟又考上研究生去了北京。幾天的輾轉反側后,我決定去上夜校。我根本沒料到,愛情也會因此不期而至。
林棉是我上夜校那所大學的學生,因為她的老鄉剛好是我的同事,所以我們有過幾面之緣。她身上的那種氣質,青春、大方、潑辣,像正午的太陽,耀眼也溫暖。學校里有片小草坪,很多學生都愛在那里看書。有時上課去早了,我也會去那里,竟然好幾次都碰到了林棉,所以也就一起看看書、討論些問題。漸漸地,在那里見面聊天竟成了我最盼望的事。我也搞不清楚,對林棉的感情究竟是愛、是羨慕還是向往,但我就像著了魔似的想要和她見面。夜深人靜時,我還會偷偷地想:她有那樣的學歷、學識,下一代肯定也會非常聰明伶俐吧?就是因為這個原因,我向林棉展開了強大的愛情攻勢。
妻子嫌我鄉下的父母太丟她的人
我們在校園里漫步,討論遇到的問題;一起吃便宜的燴面,湯湯水水都喝得干干凈凈;偶爾我們也會去街上逛逛,買些東西……愛情就這樣慢慢地滋長著,很快婚姻大事就隨之提上了日程。
結婚后,我們住在單位的一間小房子里。父母把我幾年來寄給他們的錢,又原封不動地還給了我。我買了些簡單的家具,就這樣過起了兩個人的小日子。因為工作的原因,我常常要在外面跑,所以只要我在家,就把洗衣、做飯、刷碗統統包攬下來,從來不讓林棉插手。林棉在廠里跑銷售,為了支持她的工作,我用攢了幾年的錢給她買了輛摩托車,還帶她到處拉業務。很快,她的業務量就多了起來。
2000年,我們終于集資買下了房子。我興奮地給父母打電話,要他們也過來享受享受,卻沒有想到就此拉開了家庭爭執的導火線。
本來,林棉覺得我父母來了,可以減輕她的負擔,讓她過一段享受的生活。沒想到,我母親怎么都學不會用煤氣,這下做飯成了大問題,林棉也就干脆不回家了。沒辦法,我只好給父母買了一箱桶裝方便面,前一天把水燒好了,讓他們第二天泡著吃,可林棉卻說這樣太浪費,沒有必要買那么好的。我看母親天天在樓上窩著難受,建議她去樓下和其他老太太聊聊天。母親同意了,可因為有偏頭疼,就天天包一個藍頭巾下樓。林棉看到了又是一番牢騷,說母親丟她的人了。短短一周時間,母親偷偷哭了4次,無奈的我只好把父母又送回了老家。
“門不當戶不對”的婚姻走到了盡頭
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因為愛開始婚姻的,可我在婚姻中真的沒有體會到愛。我的老家在鄉下,負擔自然重一些,可在林棉的控制下,給父母寄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;父母希望早日抱上孫子,可林棉怕影響身材,堅決不要孩子。直到婚后第8年,看到她妹妹那活潑可愛的孩子,她才頗有感悟地決定生子。
對我,林棉也始終有一些若即若離。每年年終她的單位發東西,她都不讓我到科室里搬,只能在廠門口等她搬出來;我陪她去跑業務,她還是讓我等在門口;吃蝦的時候,她嫌我剝得不夠優雅;出門的時候,她嫌我穿得破爛……我知道,她看不起我,覺得我學歷低、不夠高大英俊,太丟她的人了。我當然也有自尊,可為了維持這個家,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。
后來有了孩子,我們的分歧就更大了。她認為孩子會自然而然地長大,不需要為他操心,我則認為早期教育非常重要,一定要加強培養,所以輔導班都是我給孩子報名,領著他去的。只要我不在外忙工程,一定會去幼兒園接孩子,可林棉卻經常找借口不去接孩子……
這種生活氣氛讓我時常感覺窒息,卻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終于,一次大吵后,林棉提出了離婚。因為孩子,我猶豫了很久,但終于還是簽了字……
記者手記
每天早晨6點半,姚昆家的鬧鐘就會響起來。姚昆打開錄音機放英語磁帶,叫醒兒子給他穿衣,讓他刷牙、洗臉,然后再把兒子送到樓下王奶奶家里,讓她送兒子上幼兒園;下班后,姚昆又從王奶奶手里接回兒子,給他做飯,陪他看動畫片,父子一起泡腳,上床結束一天的生活。姚昆說,孩子需要完整的家庭,如果有一點過下去的希望,他都不會離婚的。我能看出孩子在他心中的分量,所以更擔心他今后的生活,畢竟婚姻的城堡里,還是需要一位女主人的。(文/皇甫舒敏)